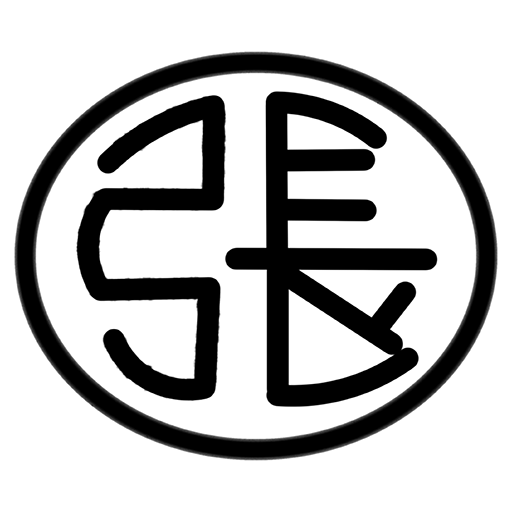為什麼要拍這部片,這部片為什麼而拍,這部片該怎麼呈現,一直是我反覆思考的問題。107年開始接觸虎尾糖鐵,從書中接觸糖業鐵路的知識也不算太少,因此自詡對糖鐵背景知識豐富,田調應該不難,所以起初只帶一個問題下去:「你對這條五分車鐵路的印象是什麼?」,這個問題是專為虎尾的居民設計,因為認為「專業知識我明白,書中也可以找,所以更需要的是從居民身上挖故事。」
虎尾街頭
108年十月,帶著這個問題南下虎尾,在虎尾街頭、鐵路邊抓人來問,忘記抓多少人了,總之幾乎都是回答:「喔!鐵路就這樣在這裡啊!冬天才會開,我們就看他這樣過去」。當下蠻錯愕的,但也開始思考,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再平常不過的的日常,人們往往會忽略平常身邊所發生的事物。因為對人們來說,他就只是「平常發生的事」,「平常發生的事」我們往往不會注意到他的特色,直到要失去了或失去了才開始了解、懂得珍惜。
後來問到一個路人,印證了我的想法,但不僅如此,也開始認識了虎尾的地方脈絡,他說道:「虎尾沒有故事,虎尾的人是從雲林各地,為了生活來往、遷居於此。你看嘛!人們因為糖廠創造了工作機會,再來有了民生產業,所一人慢慢地過來,他是流動的,他不是一個根,如果你要找故事要去褒忠、土庫、北港那些地方找……」聽到他說這段時,非常驚喜,心裡明白他在無意中說出了虎尾的故事—虎尾怎麼從一個空間到地方。雖說心喜,但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無法得到更深入的口述史料去探究。因此決定轉變田野的方式,從具備一點文史、糖廠相關背景的人身上著手。

製糖期前的虎尾街頭鐵路
虎尾驛
虎尾驛是第一代的糖鐵虎尾車站,廢站後一路荒廢到前幾年才整修,並且改造成文創店鋪,來虎尾第三年,還沒進去過虎尾驛,因為認為這種商業化的文創地方,不會講出甚麼吸引人的故事,就只會把解說牌複製貼上而已,但這次為什麼會進去呢?因為虎尾驛現烤現做的手工蛋捲實在太香了!抵擋不住誘惑,就這樣走進了虎尾驛。
既然來了,就和虎尾驛的老闆聊,認識了虎尾驛的王明輝老闆和文史工作者許鴻德老師。我向老闆談到,想了解關於這個車站的歷史,王老闆聊到:「虎尾的繁榮,就是從這個車站開始的!虎尾的歷史離不開糖業,虎尾的由來有很多種說法,其中一種就是因為以前這裡的人,冬天種甘蔗,風吹甘蔗的聲音所形成。糖廠在這裡設廠,就開始有人力需求,人們就從雲林搭著糖廠的火車,來到虎尾驛,到這裡生活定居。」老闆的敘述脈絡上與之前的路人相同,我也慢慢認知到,虎尾是一個因糖業而生的城鎮。
話說其實根據虎尾地方文史工作者所述,虎尾的地名由來根本沒有王老闆口中的和甘蔗有關,但換個角度思考,或許虎尾與糖業的關係,以深入居民的心中;許鴻德老師則提及,虎尾不是沒有故事,他不同於別的城鎮歷史悠久,但他是種海納百川所構成,如果你沒有細心體會,很難了解虎尾的「故事」。

虎尾驛
虎尾地方
與他們倆人聊後,漸漸清楚故事編排要怎麼下手。五間厝(虎尾舊地名)原本這個空間,因為糖廠的誕生,人們透過五分車鐵路開始聚集在這裡,在這裡從工作到生活的住、行也都離不開糖廠,衍生許多不同的事物,如市街、鐵支路腳工寮、紅燈區等,人住在這裡,有了回憶,有了對這裡的認同,五間厝不再是空間,而是虎尾「地方」,然而這一切的根於都是糖廠與糖廠的鐵路。

虎尾糖廠
一直在想,五分車會不會只有製糖過程可以拍,而製糖過程就是那種教課書上的標準SOP而已,較少情感和故事,因此甚至想刻意避開有跟糖廠內部接觸的拍攝,只要鐵路線上的故事就好,但實際田野下來,證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因為虎尾故事的根源就是糖廠,如果沒有進到糖廠看看,卻只是在外面喊著虎尾的故事源自糖廠,豈不奇怪?省思一段時間後,決定用透過學校跑公文,申請進糖廠看看。
田野心路
在田野的過程中,其實多數的時候,腦袋是空白的,應該說無法思考,很純粹的聆聽訪談者的聲音敘述。這些思緒,多是後面慢慢思考出來的,一開始帶回去的,只是這些口述的事實,以為事實可以直接當作故事,實則不然,如果要看事實,去看電視台拍攝的新聞就好,何須看一個導演拍一部片?在欣怡老師的指點下,我意識到,所謂的紀錄片,不是單純把眼前所見全部拍下,那樣比較接近影像資料庫的組成。所謂的故事,是把現實與歷史的物件,篩選後重新拼裝。這個過程使我折騰很久,應該說過往沒有這樣的底,所以要解放自己的想像很困難,但我強迫自己去跳脫那個既有思維、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