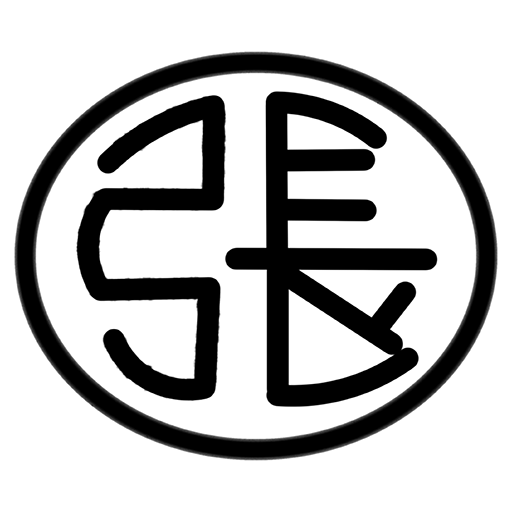與五分車的相遇
原本沒有很喜歡台糖的五分車,因為它離我生活很遙遠,我生在北部,而五分車大多在中南部,且除了後來的觀光五分車之外,五分車我們基本上是搭不到的,畢竟真正載客通勤、交通的五分車,很早就沒有行駛了,所以對它沒有什麼情感。
直到有次在圖書館翻閱到許乃懿老師的《台灣糖鐵攬勝》後,才開始「入坑」,然而矛盾的是,我竟然是因為五分車那種不同於平常生活中對鐵路的印象,而被它深深吸引,開始關注它。五分車是輕便鐵路,可以說介於我們熟知的台鐵、高鐵、捷運,那種制式的鐵路與早期的輕便台車間,這也就是五分車的魅力所在,有屬於自己特有的文化和學問。
虎尾糖廠為全台灣最後一所,還在以鐵路運送甘蔗原料至糖廠製糖的糖廠。107年製糖期,心血來潮特地跑到虎尾,至糖廠旁鐵路沿線等候,不久看到小火車拉著長長的甘蔗車廂浩浩蕩蕩地駛來,彷彿小時候在許乃懿老師的《台灣糖鐵攬勝》中的景象,本來以為消失的、只能在書中看到的情景,如今卻在眼前。沿著鐵路,到北溪厝附近,另一班小火車從遠方緩緩地駛來,當下高鐵又從上方飛躍而過。心想,自己生在二十一世紀,卻還能看到上世紀留下來的活化石,心中的百感交集,充滿興奮、驚嘆與感動。

初次見到虎尾五分車的景象

五分車與高鐵交會,一種神奇的時空
為它寫下故事的發想
台糖五分車是很特別的東西,世界上有糖業鐵路的地方不多,台灣是其中之一,而且又發展出獨特的文化。他造就一個地方的繁榮、見證台灣從農業到工業化的過程,背後的故事讓許多前輩花了大半輩子再研究,然而時過境遷,台灣的糖業鐵路也從興盛走向凋零。正是因為這樣的獨特性、豐富性,以及快消失,希望自己也能為他做些什麼。此外在申請百川面試那天,有個老師問我,走台灣這麼多地方,印象最深刻的景象是什麼?我直接回答虎尾糖鐵,正是這種神奇的魅力,讓我被深深吸引,因此想透過影像的拍攝,替他寫下屬於他的故事。
藉由實地走訪、影像紀錄的方式,從製糖期開工開始,去認識糖業鐵路文化的脈絡及當今現況。從糖廠配車所出發,穿過虎尾市區,沿著鐵路,跟著火車到蔗埕,去尋找藏在這條鐵路旁,關於城鎮與糖業連結的故事,或許是地方居民的回憶,或許是看柵工們頂著大太陽下辛勞的點點滴滴,又或者是蔗埕工人和司機師傅們,所經歷的故事。
糖鐵和台鐵、高鐵、捷運相比,是截然不同的生態,距離遙遠,但他更深入許多城鎮和村落,雖然他很少載客,但他是富有人情味的、有溫度的、有故事的,是屬於我們難能可貴的文化資產,所以想帶大家去認識他,又或者說,在即將「被自然淘汰」的今天,我們不知眼前的這些,突然有一天,成為回憶。
最後的五分車與地方誌紀錄片
對於拍攝鐵道影像的人來說,理由多數是紀錄這個時代的鐵道風情,留給後人看,見證鐵道在某個時代下的樣貌。我們過往看到前輩們的照片、影片之所以會覺得珍貴,要知道那個時代並非人手一機,且鐵道是國防機密,資訊也沒有現在網路發達,造就了鐵道攝影的稀有性,賦予了這些影像價值。如今人手一機、資訊爆炸的時代,鐵道攝影已經不再具有稀有性,台灣有數萬名鐵道迷在拍火車,單純的「留下紀錄」還有意義嗎?
推展鐵道文化是鐵道攝影的宗旨,因此勢必將影像故事化、節目化,才能賦予更深的價值,當然節目化新聞專題很早就在做,近年網路媒體也不少做鐵道議題的,我當然不會傻傻地跟他們競爭;而故事化拍攝鐵道紀錄片、電影的也不少,如蕭菊貞、黃邦銓、黃威勝都是,不過他們都是以鐵道上的人物、或是自身作為敘事主題。
就如前面談論地方誌與民族誌所說的,台灣地方誌類型的紀錄片不多,當然更不用說在鐵道這個主題上。我一直認為對於鐵道文化最重要的,是地方脈絡與情感,空間變成地方而有了鐵道,而鐵道又擴大了地方,因此我們何不嘗試做鐵道地方誌紀錄片呢?這是最後的五分車創作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