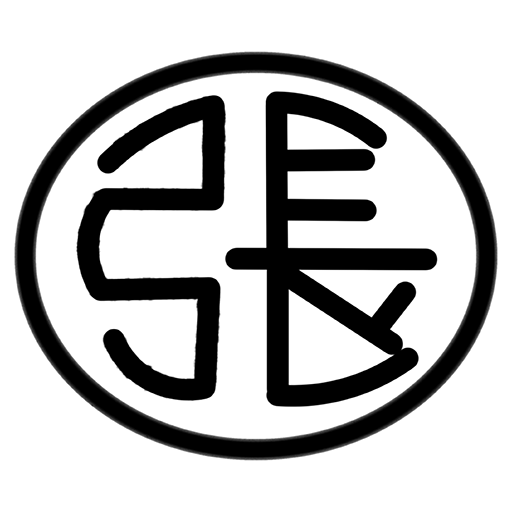對於紀錄片的創作,有三個重要的元素—文本、影像、聲音,這些元素互相交織,觸動觀眾的感官,形成完整的作品,缺一不可 。這部片是一種嘗試,在影像與故事的交織裡,有許多未知和疑問,有許多以前懷疑的、或是不敢想像的,把這些問題與嘗試圖用在這部片裡,透過實際的經歷,尋早答案。
文本
紀錄片的文本,我一直都是寫個大綱、寫個方向,不會像劇情片一樣寫個完整的劇本,因為紀錄片是隨時在變動的,從一開始的田野開始構思,隨著拍攝的進行、剪輯的調整,其實到最後一刻才會決定最後的文本,因為前面所想的,往往會和後面實際有很大的落差。
影片最前面的地方,用模糊扭曲的盡頭,配著我走在雜草叢生的鐵路上,路人與我對話的聲音,象徵著「田野者」探索未知的鐵路。而接著影片的敘事軸跳到田野者進到虎尾這個場域,搭著客運來到虎尾、走在虎尾街頭,隨著田野者的聲音開始,故事開始。
這部片的故事,從【虎尾印象】開始,有人認為虎尾沒故事,但耆老認為虎尾的故事是海納百川,故事在這裡停下,留個何謂「海納百川的伏筆」。
下一章【糖鐵淵源】,岔出去從台灣糖鐵的歷史開始說,最後耆老帶到為何糖業最後選虎尾,從這個章節開始,開始一連串的介紹虎尾糖廠的糖業與鐵路運作。【關於馬公厝線的二三事】從糖廠開工開始,涵蓋敘說了馬公厝線的介紹、糖業鐵路的運作,還有看柵工、站務員、司機……的故事,接著【甜蜜工廠】帶到糖廠運作的流程,抽樣過磅、製糖工場如何製糖、砂糖倉庫。
這些部分看起來都圍繞在糖業與鐵路的知識上,但下個章節章會告訴你,這樣的一切,其實正呼應了耆老所說的「海納百川」。在【鐵支路角】的章節裡,漢鵬老師說到:「虎尾的歷史從糖廠開始,如果要了解虎尾就要先了解糖業。」,後面就開始敘說虎尾與糖業的脈絡,再次呼應前面的「海納百川」,如果沒有這些製糖的工業文化,就沒有今天的虎尾。
最後在接近尾聲的地方,安排了【小火車的未來 觀光?】,拋出五分車現在面臨的議題給觀眾思考。而影片最終的地方,一如往常的,安排了導演—「我」對於虎尾五分車的省思。畫面跳到製糖結束的寧靜,糖鐵好像過了製糖期就被人遺忘,不知來年會不會重新開始,故事結束。
影像
【影像】
承載故事腳本的容器
或者你可以說它是訴說故事的媒介
我們使用鏡頭語言呼應故事線,
透過鏡頭的視覺,勾起觀眾的感官
進到故事的世界
搭配旁白與字卡和剪輯
依循著文本
為整個故事架構鋪成
—–
【模擬鏡頭】
如果事實無法透過現實的當下呈現
那可否透過虛構的模擬去替代?
虛構的影像可以乘載事實嗎?
還是眼前的現實才是虛構?
如果我想呈現我的心境,
那種抽象的東西,
又能用具體的影像呈現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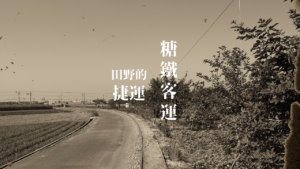
—–
【顏色】
使用調色去呈現作者拍攝時
身體、眼睛感官所接觸到的環境訊息
對我來說,一個環境所給人感官帶來的溫度
決定眼中視界的呈現……


我喜歡高對比、鮮豔的影像
它們能夠直接把影像拍攝時的環境感官帶給觀眾
給觀眾一種「有溫度」的衝擊
也用冷暖色溫
去告訴觀眾影片中畫面與文本契合的心境
或是說導演對於畫面的感知
—–
【放慢影片的節奏】
記得跟九番阿嬤聊天時,她提到有個外國人來拍虎尾糖鐵,後來她有看到那個影片,她說到:「影片鏡頭速度好快喔!看了好暈,根本不像我們的五分車!」,後來去找到九番阿嬤口中的影片,那位Youtuber其實就是用最主流的手法,每個鏡頭大多2~3秒的快剪去製作影片,但就如九番阿嬤所說的,感受不到五分車在影片裡;另外也找了電視台報導虎尾五分車的節目,看了差點吐血,電視台居然覺得五分車開太慢,所以剪輯時把拍攝五分車開動的影片素材,全都加快約2倍速度!整個完全失真。
五分車與虎尾的慢步調,是必須要透過捨棄主流,使用較慢的影片節奏進行的,如此才能在影片中呈現五分車給人的感觸,所以後來大多使用緩慢、長時間的鏡頭,對應五分車並非一般印象火車的快速,它用屬於自己、屬於這個地方的步調,穿梭在田野與街道中。
聲音
【音像】
導演錄音的旁白呈現導演「外來田野者」的角色
拍攝時雖然有很多訪談,或是聊天
可能是與當地人、工作人員,或是其他專家們
但只使用訪談音檔作為旁白
這些人們,都是在歷史的洪流中,
默默地存在,有趣的是歷史卻是
由他們聲音轉化成的文字而成
卻沒有留下他們的名字或身影
而我只是巧合下經過這段歷史,
在談天中意外得進入他們,
得到他們的故事,幫他們留下最真誠的聲音與身影
在這部片的故事裡,他們是主角
但在整個歷史中,他們往往只被當作是配角
—–
【音樂】
影像就如同是一道菜的食材
而配樂只是讓整道料理
產生層次及突現原食材風味的佐料
先讓作曲師透過影像,甚至是實地走訪
去了解到「虎尾」的地方環境感官和對五分車的感觸
為影片配上屬於虎尾五分車的曲子
讓觀眾在觀影時
能透過配樂與影片、敘事的交織
更顯著的帶起心中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