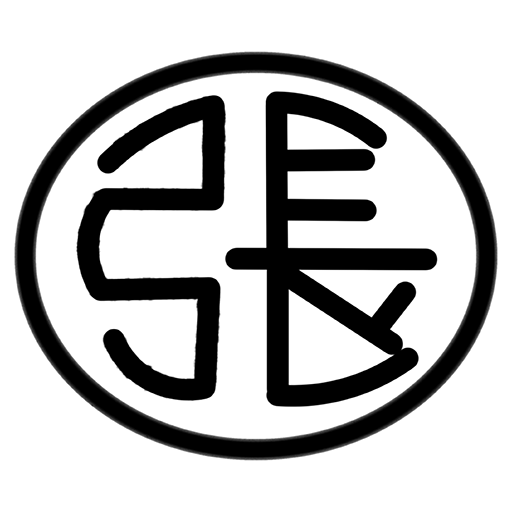這部片登場許多角色,象徵了虎尾由空間到地方的關鍵人物組成,可能是居民、耆老,可能是糖廠職員、包商臨時工,也可能是專家、學者。在這部片裡,可能不會看到規規矩矩的坐著訪談他們,也不太會拿鏡頭貼著他或拿小蜜蜂來收他們清晰的聲音。只跟他們聊天,聊他們對於地方的回憶,或許看起來很隨興,但我認為,這樣才能獲取他們最真誠,對於地方的感受。
歷史是由他們所構成,然而歷史卻不會記得他們,他們的所在行成了歷史的框架,但卻被埋沒其中,文獻不提及他們的姓名,也埋沒了他們的聲音,就如同他們的聲音被環境所掩蓋,你聽的到,但是覺得雜音很重。
外來的田野者—導演
導演也是這部片裡,其中角色之一,我把自己設定為一個「外來的田野者」,以旁白的方式呈現,從外人去體會地方的環境感知內化的過程,對糖業鐵路有一定的基礎知識,或許帶有一點點學者的味道,來到虎尾這個地方探索,欲尋找糖鐵在虎尾這個地方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在這部片的角色工作就是聆聽以及感受,進入田野的場域裡探索,把所聽到的或感受到的做內化詮釋,虎尾就是這部片中,我的田野場域。透過這個過程,去感知虎尾地方。或許你也可以說我是田野詮釋者,與田野對話,去把事實拼裝成屬於這個地方的故事。
記得一直有人問,為何旁白不用台語說?其實曾經考慮做台語版,把所有導演旁白全部改為台語配音,但後來作罷,因為仔細的去想,如果用台語配音,角色的設定可能就不再是「我」這個外來田野者,所有旁白都是根據「我」這個外來田野者所設定,如果更動角色,旁白勢必也要改。我是客家人和外省人,台語對我來說是陌生的,我用我的語言和虎尾的台語對話,不正是呈現文化間對話?這也是最後堅持我的旁白用普通話的原因,沒有必要為了看似貼合在地,去假裝自己。
記得第一次來到虎尾時,感覺到了「國外」,身邊的人都和自己講不同的語言,甚至很多中、老年人都不會講普通話,我只能比手畫腳的溝通。語言文化的差異,也成為日後田野上,其中的一大難關。
資深糖鐵專家—許乃懿
許乃懿老師是台灣資深的糖鐵專家之一,也是《台灣糖鐵攬勝》的作者,算是我的啟蒙老師。
網路的無遠弗屆,讓我在長大後認識這位「寶典」的作者。兩年前曾經特地南下嘉義找許乃懿老師,請教許老師關於台灣糖業鐵路的故事,當時的訪談有錄音錄影,本來想將聲音拿來這部片使用,作為敘述台灣糖鐵史的部分,但發現錄音音質太差,環境音嚴重蓋過老師的聲音,因而作罷。
今年製糖期雲林記憶cool舉辦追五分車的活動,特別邀請許老師來當「導遊」,我特地抓時間去突襲許老師,當初其實是想拍攝許老師跟「觀光客」們講解史的片段,作為〈小火車的未來 觀光?〉那一段的素材,但後來查帶時發現,許乃懿老師在解說的內容,可以直接用在甘蔗採收與蔗埕運作過程,還有為什麼要用火車運甘蔗。
老師在這部片裡面的角色,放在糖鐵運作的流程中,訴說糖鐵相關的知識,有點類似文史工作者,不過不同的是,許乃懿老師的「老師」形象強烈,在影片中聽到他與遊客的對話,老師傳授知識給遊客,可以觀察到這一點。算是整部片裡面唯一帶有「學者」色彩的角色。
虎尾驛老闆—王明輝
王老闆在這部片裡的角色,算是在地居民,也是這部片的主角之一,透過它自身在這個地方的成長,對自己家鄉的理解,並給「外來的田野者」說故事,我則將他所說的故事,去與其他角色或我挖掘出的故事、事件結合,編排出整體的故事。
從田野到拍攝的過程中,總是會抽時間到王老闆那邊休息,邊跟王老闆聊天,一邊錄下王老闆的聲音。王老闆的聲音是非常有溫度的,他的聲音是虎尾鎮民對於地方的印象,其實就是所謂的在地觀點。
在學術上,這種小民的聲音常常都是被忽略的,就算有了田野調查,往往也是用宏觀的尺度去看。而這些在地觀點,的確就學術來說,可能微不足道,因為可能透過太多外在因素影響,有點道聽塗說,知識性不足、錯誤,但這些「道聽塗說」真的毫無可論性嗎?我的想法是否定的!走訪幾次田野下來,某種程度這些在地觀點,雖然說不上是「歷史」,卻充分了反映居民對在地的印象與情感。
雲林記憶COOL—李漢鵬
漢鵬老師是資深的文史工作者,致力推動文化資產的他,也是許多地方文化局處的頭痛人物。我在虎尾驛認識漢鵬老師,那天雲林記憶COOL的「雲林講古」邀請了退休糖鐵司機—程孔昭老師來訪談。當時其實是為了程老師而去,也錄了幾段,可惜最後沒有用上。結果反而因此認識了漢鵬老師,知道他在在地作文史後,就一直希望有個機會訪談他。
雲林記憶COOL那年開始推「追五分車之旅」的活動,趁這個機會去訪談漢鵬老師,順便跟他多認識交流。漢鵬老師是在所有的主角當中,唯一用標準的訪談片段的,就是受訪者坐再鏡頭前說話的那種,不同於製糖工場鄭建家股長的片段在現地場域訪談。會這樣安排,是因為認為訪談漢鵬的主題—小火車的未來,是一個沒有溫度的議題,他不是回憶或故事,是一種大家坐下來討論時事的感覺,也因為是「未來」,所以沒有現地可以合適的呈現,最後用這樣的方式呈現,想呈現一種會議、討論、與議題面對面的感覺。
漢鵬在後期幫了我許多忙,影片結尾的地方,我騎著腳踏車追火車,那個腳踏車就是透過漢鵬從雲林記憶COOL借來的,在此之前我沒有騎腳踏車追糖鐵過,都是徒步或公車,而片尾的腳踏車是想呈現一種意象,就是一般人或其他鐵道迷,特地來追五分車的樣子、感觸。
虎尾站—林安登
林安登是今年新來的虎尾站務員,身為「糖廠子弟」的他,回到兒時熟悉的場域,與「新手」的身分有著強烈的對比。他對我來說不只是一個站務員,我也不把他當作新手看,某種程度來說,他是居民與糖廠連結的見證,剛來到這個場域工作的他,卻有著說不完的回憶與故事。
訪談時除了在影片中可以清楚看得的車站工作內容外,其實「田野的捷運」中第二段的旁白,也是林安登先生口述的,我向他提問糖鐵客運的事,他熱情地分享。在影片的背後,林先生也聊了許多他與糖廠的故事,糖廠子弟從小生活就總是在糖廠身邊,從搭糖廠火車通學,到洗澡去糖廠公共澡堂等,甚至還有聊雲林各庄的台語口音差異。
攝影機的背後,其實話了許多有趣的「日常」,有時也會想,這樣的日常,會不會可以成為另一個有趣的故事。
鐵道迷—蕭任宏
蕭任宏是我大學的室友,特別請他來擔任「主角」之一,正是因為他不僅對鐵道有濃厚的興趣,出身北部、小康家庭的他,對他來說鐵路圍繞在高鐵、捷運等現代化的鐵道運輸,就如許多年輕人一樣,對糖鐵是陌生的,而對鐵路的興趣,也會使產生熟悉又陌生的矛盾情感,與在地耆老的回憶、文史工作者的想像,顯得強烈的對比。
所以這次特別請他,算是刻意安排讓生於現代都會的人,與糖廠、鄉鎮,在許多人的刻板印象裡,是已經或快要消逝的事物交會,看看會產生什麼火花,跳脫在地、耆老、專家的觀點來看糖鐵,呈現多元的對話。
製糖工場—鄭建家
製糖工場的鄭建家股長,是製糖工場內製糖流程的導覽,他登場的時候,或是聽到他的旁白時,就是在做糖廠知識介紹的時候。鄭股長的角色定位比較特殊,既不是主角也不算是小人物,他的對白,也不太是故事,偏向專業知識的簡介。
一開始有想大幅刪掉鄭股長片段的念頭,因為整體過於知性,且以糖業的製程為主,並不是我主要想呈現的,但後來因為爬梳整個虎尾地方的脈絡,認知到「糖業」對於整個地方的關聯與重要性,才決定適度放上這一段。
司機—陳瑞鐘
司機的拍攝,隨著鐵道股通知無法跟車拍攝的消息後,就差點被遺忘了!好在路程景拍攝的技術問題,多花了幾天拍攝,因為拍攝路程景架攝影機的關係,會和司機員們接觸,這也才讓我想起,要拍攝司機員們工作的日常。
雖說有接觸,但其實接觸的時間不長,我趁最後一次拍攝路程景時,與司機搭話、聊天,同時也錄影拍攝。當天攝影機是跟116號機關車,司機員是人稱「國民黨」的陳瑞鐘先生,因此就由他擔任司機員這個身分的主角。他之所以會被叫「國民黨」,據說是因為他處事為人的關係,這邊就不多提了。
我還蠻喜歡國民黨大哥,在「聊天」的過程中,他很樂意分享工作上的日常,也喜歡話家常,整體的拍攝非常順利的進行,短短半個小時就可以把該要的素材取齊,幾乎沒有什麼壓力。
另一個會原因,是因為他是我遇到的三位司機裡,最認真的一位。舉例來說,有些司機都是八點發車時才在車庫出現,引擎一發動就出車了!這樣根本沒什麼內容可拍,但國民黨大哥老早就出現在車庫,按著流程檢查車子一遍,才啟動引擎,而且也因為他會提早待命,我才有機會可以多跟他聊。在與他相處的短短時間裡,也可以從他在行車上的執著發現,他對安全的重視,這種執著也高過其他司機員。
車長與實習司機
在虎尾糖廠內駐點時,剛好那一年有招新司機,正好去糖廠裡拍攝的時間,一位資深的車長在帶新的司機進行場內調度的教育,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了解更多糖鐵運轉的知識,我便跟在他們旁邊,一邊拍攝以一邊「聽課」。
這段拍攝裡,人物的身影不是主要重點,所以很少去特寫車長工作或是新司機學習的身影,重要的是師傅帶新人時的知識解說,同時也用另一種方式的對話—讓觀眾彷彿化身為新司機,跟著老師傅進入虎尾糖鐵的現地場域。
這位新人實習司機,據鐵道股股長說,好像是大學剛畢業,報考台糖特考被分發過來的。以前我一直以為虎尾沒有再招新司機的可能,擔心糖鐵會被「自然消失」,今年招了年輕的新血進來,老糖鐵終於有了傳承,心中百感交集。
拍攝時,我已經忘記攝影機的存在,把自己融入他們的課堂中,或許是鐵道迷好學的基因發作,試著把自己當成實習司機一樣,吸收師傅教導的知識,甚至還在中間遇到聽不懂的地方,直接舉手發問,在這個當下,我不是導演。
倉庫工人
倉庫工人是整部片裡,唯一的無聲主角,他們不用透過具體的「聲音」,而透過工作的身影,傳達他們的故事。在拍攝時,他們裸著上身、流著汗水,搬著五十公斤的砂糖,是最有張力及溫度的畫面。過程中不必特別與他們交談,便可感受出其中的情感。
搬運工是虎尾最具代表性的小人物之一,當年糖廠所需要的大量人力、讓虎尾從村莊變成城鎮的人流,大部分就是由他們組成,因此他們給我的感觸,如同虎尾這個城鎮的歷史,戲劇性的在眼前「真實演出」。陶醉在他們忙碌的身影中,不忍心打斷他們,也覺得他們的畫面,不需要特別用額外的聲音或文字註解,留最純粹的感官。
十三番—徐文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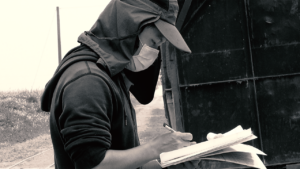
裝車場工人的拍攝,選鐵路的終點—十三番裝車場,在那邊待了一整天,去與裝車場的工人聊他們工作的過程與經歷。裝車場我並不是初次前往,過去就有多次前往裝車場的經歷,也對裝車場的運作有一定程度熟悉,不過都是在九番,這次利用拍片的機會,想說前往從未去過的鐵路終點—十三番裝車場。
十三番裝車場的工人其實有三位,以徐文啟大哥為主要的拍攝主角,他是約耕股的工作人員,在走訪虎尾糖鐵的田野中,他是很特別的一位,徐大哥跟我年紀相近,是剛出社會的新鮮人,同時也是北部客家人,照理說他不太可能出現在這個場域,但卻因緣際會出現在這裡。或許是年紀相近、又或許是同事北部人,覺得比較容易親近。
過程中,我一樣以拍攝他們工作的過程為主,但比較不一樣的是,在他們工作時,我會直接拋問題問他蔗埕的工作細節,直接拍攝下來,有點像一般紀錄片或是新聞的拍攝手法。
這段拍攝可惜的是,訪談徐大哥的蔗埕工作知識很片段,無法串連整個蔗埕運作的流程,最後只能透過許乃懿老師跟陳敬恆大哥,彌補缺的素材。
看柵工—張阿同
阿同大哥是我第一個認識的,也是最熟悉的看柵工,在還沒熟悉之前,他就總是認得出我,而且不是應付的那種,是真的把我們過去聊過的內容掏出來。
或許是因為在拍紀錄片之前走訪虎尾看糖鐵,就常常跟他聊天,問他列車的運轉資訊,或是糖鐵的運作,所以他對這個從外地來的認真鐵道迷印象深刻。而這次利用拍攝的機會,讓他成為「看柵工」的主角之一。
阿同大哥是土庫人,以前在化學工廠當工人,退休後覺得待在家太無聊,所以來虎尾做看柵工。廠前大門的平交道因為常有違停,所以很難管,同時也是工時最長,因為糖包車的關係六點要上工,最後一班車進廠才能下班,而且要一人同時故兩個平交道,被分配到這個點的人,通常做沒多久就離職,原本阿同大哥也想在拍攝的前一個製糖期提早「退休」,但想想在家真的太無聊,所以又繼續做下去,很神奇的緣分,讓這位熟悉的看柵工成為這部電影的主角。
看柵工—蘇家父子

蘇家父子是虎尾市中心的看柵工,父子二人共同首一個平交道。因為位置的因素,他們所在的平交道,幾乎是每次去虎尾,第一個蹲的點,我跟他們的交集沒有到阿同大哥這麼濃厚,不過也算是認識,會打招呼、會閒聊。
他們在影片中的角色是看柵工除了阿同大哥外的另一個主角,但性質比較單純一點,呈現的就是看柵工這個角色,他在日常工作的過程,所經歷的事物。
九番阿嬤—許滿祝
九番阿嬤是這條鐵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年邁的她有許多關於這條鐵路的回憶與故事。
或許是因為她本身的經歷資深,外加在這個列車交會的「特殊地點」,再加上她好客的性格,使九番阿嬤成為這條鐵路上的大紅人,甚至可以說是代表人物。許多鐵道迷或遊客來到這裡,會來找九番阿嬤聊天,從阿嬤口中獲得關於這條鐵路的歷史與故事。
九番阿嬤的角色其實在這部片裡面,擔當「外站站務員的角色」,她帶來的故事是交會站站的運作。同時因為她的資深,所以也能跟我們述說過往與現在的對比,例如站務人員待遇的演變,列車管制方式的變化。
近年來一直有九番阿嬤要退休的傳言,畢竟阿嬤已經九時左右的高齡,退休其實不怎麼意外,雖然某種程度來說,少了九番阿嬤好像馬公厝線就少了甚麼,有點不捨。但後來我們再度去陪阿嬤聊天時,向阿嬤聊到此事,結果阿嬤對這個「新聞」渾然不知,不知道是誰在傳的,不過對於是否要退休,阿嬤說:「如果大家還希望我在做,那就繼續吧!在家也無聊。」
但我猜阿嬤應該是有轉變過想法的,因為他也跟我們提到,她有動過大手術,身體沒有說到很好,一這樣的情況其實一般人早就退休了!不過隨著虎尾的糖鐵文化開始被推廣,阿嬤也變成了「大紅人」,有些遊客甚至慕名前來找她,或許也因為這樣,讓這份工作又多了樂趣,才讓九番阿嬤想繼續做下去。
鐵道文史工作者—陳敬恆
陳敬恆是台大火車社的前社長,現為交通文資學會的常務理事及鐵道情報執行編輯,算是前輩,高中時參與台大火車社的社課而認識。其實在拍攝虎尾之前和他大概就只有一面之緣,也沒談過幾句話。
直到這部片在後製的時候,剛好當時他在做文化部糖鐵文化路徑規劃的案子,所以當他得知我在拍虎尾的片時,就傳訊息來「關心」,這突如其來的關心,起初讓我覺得他是在表示敵意,叫我不要跟他們的案子做衝突,但後來多聊後才知道,是我多慮了!他單純基於文資的精神,來關心同樣在這田野耕耘的人。陳大哥一直關心這部片的拍攝情形,同時也大方的提供協助從前面被抓來當其中的角色旁白,到後面的雙語字幕翻譯,我非常感謝他願意大方的願意幫忙;甚至也幫忙推銷到台大火車社,由他牽線,讓我的試映會其中一場辦在台大,也同時擔任該場的與談人。
陳大哥在這部片裡擔任是一個與田野者、田野對話的專家的角色,起初並沒有安排他的加入,直到後面後製的尾聲,我覺得有些地方的旁白,因為偏向「地方」的專業知識,用田野者的旁白有種「都是導演在講、過度主觀、缺乏對話感的感覺。」因此我邀請陳大哥擔任那些要替換掉的旁白聲源,呈現一種田野與文獻間交融的感覺,而陳大哥也爽快答應。錄音當天也很有趣,正值補拍新營通券素材的那天,他問能不能跟,來參觀我的片場,因此我們就在新營果毅後旗站旁,完成了這段錄音,我自己的想像裡,或許這樣的錄音,某種程度也作為無法取得虎尾環境聲音紋理套在新錄製旁白中的替代,使得那種「訪談對話」更趨於現實。
未留下姓名的小人物
他們可能只是路人,但卻從他們身上,或者與他們交談的過程中,得到更多關於地方的回憶。
記得前面提到,那個說虎尾沒有故事的人,我不認識他,他也沒留下名字,但他對虎尾的記憶,卻成為了田野者給予「最後的五分車」的故事脈絡。有的時候紀錄片不一定要找什麼有名的人、事、物,那些很知識、很教條的大道理,才能寫下故事的開頭,反而那些無名的小人物,他們記憶更能給故事埋下深遠的伏筆。
在田野捷運那段,前面的旁白是和一位路人阿伯聊天的對話,當時是製糖期尚未開始前,我沿著被雜草淹沒的鐵路走。那位阿伯騎腳踏車經過,看到我在拍鐵路,就主動上前聊,聊起以前公路不發達的年代,雲林各地都靠糖廠小火車往返的日常。簡短的對話裡,或許在別人眼中只是話家常,但對一個田野者來說,是刻在田野對象心裡的回憶,是珍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