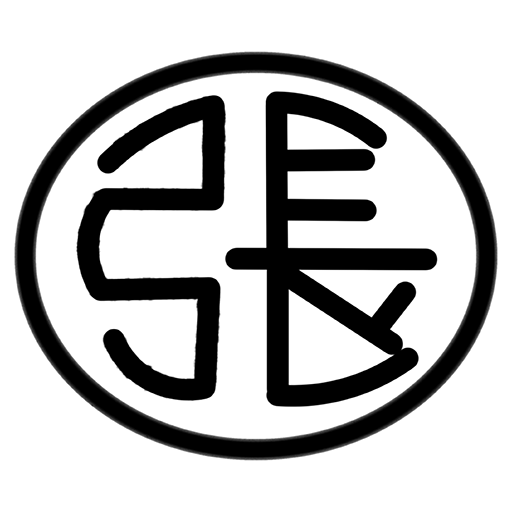片名
漫長一詞象徵常民記憶的零散、深遠的特性,同時亦象徵田野者展開長遠的旅程探索,深掘蘊藏的地方故事,省思行動本身、影像、常民聲音對自身的關係。
五分車代表糖鐵常民記憶。根據目前田野調查的結果,「五分車」、「五分車路」等詞彙以散點式的流傳於民間,以口語非正式的語態代表糖業鐵路,其中以雲林以北較為普遍。根據黃偉嘉先生口述於南投地區的田野調查結果,認為五分車在早年中南線2、濁水線3運作時,當地常民已普遍使用在對於台糖鐵路的稱呼(黃偉嘉,2022);王翔先生亦表示在過去田野調查經驗中,五分車一詞零散的出現在中南部鄉村的常民話語中(王翔,2022)。因此某種程度而言,五分車、五分路可做為糖鐵之常民記憶代表。然而田野調查中發現,嘉義、台南、高雄地區對於糖鐵的稱呼大多以「小火車」較為普遍,反之五分車較少,甚至部分地方未曾聽說。因此為尊重各地常民記憶中對於糖鐵的稱呼,因此亦加入小火車一詞,故將片名定為《漫長五分路/小火車》。
問題意識
糖鐵未來性在於糖業鐵路面臨消亡的今天,我們是否得以在過去鮮少探索的領域中,探索不同面向的可能。今日主流對於糖鐵文化的思考—出自官方的糖業史 、鐵道史 、冷戰史 層面形成的歷史框架,從張崑振的《再尋冷戰軌跡 : 台糖南北平行預備線文化資產價值研究》 的南北線鐵道價值評估(總結)中,「其價值具體可歸納為歷史事件—國共內戰、特殊社會與經濟價值—台糖公司戰後轉型、地方交通、特定發展時期代表—美援、建設技術、稀少性」(張崑振,2020:165),幾乎圍繞在糖業、鐵道歷史及台灣冷戰史;在田野過程中,觀察現今接觸糖鐵相關文化工作者所談論內容,也圍繞在糖鐵營運、車輛的細節上。由此可知,南北平行預備線正是此歷史框架的集大成與象徵,並將此塑造為糖鐵文化,試圖推廣。這樣的文化,實質而言是國家政策 、台糖商業考量 脈絡的轉化與投射。
但我在田野的歷程中發現,除了專業文史工作者、鐵道迷之外,多數情況對此脈絡是有所差異的。正因為這樣形塑的糖鐵文化,只圍繞在國家政策、台糖商業政策的脈絡中,與一般常民脫節。生活在鐵路旁的常民真正的記憶,似乎無人關乎他們怎麼看待身旁的鐵路,儘管張崑振在其著作 中提到「南北現在社會文化價值的體現上,延伸呈現台灣傳統社會、傳統漢人家族文化」(張崑振,2020:143),但並未詳加說明此部分,僅一語帶過;而田野中,文史工作者他們在自己的田野中雖然會大量訪談在地常民,但以鐵道資訊取得為主,鮮少探討鐵道與地方生活的關係。
常民難以曉得我們熟知的南北平行預備線歷史脈絡,實際田野下來也證實如此,僅有極少數常民提及家門前的鐵路與戰備有關,因為當時時代背景,這屬於國防機密;而對鐵道的理解如我們現在搭火車、捷運的經歷一樣,雖然是搭乘的日常,但不見得知曉背後的營運、甚至是土木建設。因此拘泥於鐵道史、台灣冷戰史終究無法讓地方的族群意識產生共鳴。
以常民記憶出發的意識形態在於,常民記憶的蒐集是位於以上所提到的歷史框架之外。在此歷史框架外,是否有更多過去所忽略的?未知的?常民記憶來自於自身對於生長歷程中的印象深刻,或許是地方過往繁榮的光景、亦或者是單純無壓力的生活日常、又或許是對於自家土地的印象,這是常民記憶珍貴所在,與冷戰下的國家政策、資本主義下的台糖商業活動呈強烈對比。此外歷史是相對有限的,常民記憶出自在地居民對自身所處地方的詮釋與想像,相對是無限的,因此具備延伸性。
方法論
在常民記憶的蒐集過程,亦思考本計畫所謂的「常民」為何?從以上問題意識的梳理可知,「常民」在此被作為跳脫歷史框架的形體,因此這次的作品常民的範圍訂定為「居住在糖鐵路線(南北線)周圍地區者,並非台糖直接相關人士,非專業文史工作者、學者」。
田野者本身台糖相關人士,也非專業文史工作者、學者,因而作為常民之一,回顧《崁子腳五分路》 的思考,田野者的常民與在地常民的角色性質、話語權還是有所差異,「田野者具有相對強大的話語權、話語決策權,以及對於糖廠、鐵路、地方的印象及感官,多來自於歷史及過往自身探索經歷的轉譯與投射」(張貽帆,2022) 。當田野者開始田野踏查的行動,其自身的話語權就必定會顯現,從田野地方的選擇、探索對象的選擇,到是否將一個他者的話語顯現,皆是田野者的意識形態展現。因此田野者雖作為常民,且作為外來者、後生仔,在常民記憶的話語中有求於在地常民,看起來話語弱勢,但實則不然。因此為了達成前述問題意識中,將常民記憶的話語能最大的方法,凸顯在地常民記憶的話語、勢必在處理上需降低田野者的話語呈現,以相對平衡兩者之間的衝擊。
本作品之在地常民記憶的呈現,將與聲音、口傳敘事的方式呈現。在話語的表達中,言說的聲音是最凸顯的方式之一,我思考到在傳統社會中,一切的敘事與文化多由口傳方式,一層一層的從長輩傳至後生,並在流傳的過程中隨著參與過程的個人,增添、捨棄內容,因此有所轉變。我想所謂的常民記憶就是如此成型,因此透過採集在地常民記憶口傳敘事的選取與呈現,將田野者作為傳播者之一,而非主導話語權、言說的地位,故事並非言說者編撰、而是傳承聽來的、非歷史的。其同時所象徵的正是前述脫離歷史框架啟發多元性、延展性,是為在地常民話語凸顯、田野者在話語權上的沉沒。口傳本身藉由聲音傳播,傳播過程本身融入傳播者—在地常民自身的感官詮釋,而非文字牢固、定型的訊息輸入,口傳其特性相對較具備延伸性、並更大程度展現在地常民未能凸顯表達的感官及話語,不僅與歷史將有所異同,同時增加在地常民的話語權。
田野者除本身行動具備話語權外,在行動後接收來自在地常民流傳的故事,或自身探索於地方空間所感知,亦將行經田野者,並納入田野者的自身經歷、感官後輸出。以影像建構我的話語,是我在這場田野中最直觀的選擇,影像的視覺傳播在選取拍攝影像、構圖、運鏡方法上建構田野者的思考,而影像與文字、口傳不同的是,當其在傳播於觀眾時,觀眾並非直白的接收,而是需透過腦中的解讀、轉化後才成為訊息,對流傳至觀眾而言,將觸發更多的衍生性。
紀錄片地圖製作
在以上梳理後,亦思考「糖鐵的常民記憶」是否適合用連貫的敘事形式呈現?儘管我們是沿著南北平行預備線的文化路徑進行踏查、探索,但在田野過程發現,不同地方所採集的故事縱然有不少共鳴點,但具有高度的獨立性—屬於對地方的想像。因此我思考到這部影片是否適合用線性的敘事框架套用?線性的框架不僅限制的常民記憶的無限性、延伸性,且無法尊重地方的獨立性,因此我認為更適合以點狀的、零散的形式呈現。
觀眾對影片時間軸,易產生要求影片具備起承轉合、連貫敘事的期待,這與點狀的、零散的敘事相互牴觸。點狀的、零散的敘事若置入連續的時間軸中,到中後段觀眾將會感到倦怠,會影響到觀眾對於不同地方常民記憶敘事之間的感觸。將各個地方的常民記憶攤平呈現,跳脫影片的時間軸框架呈現。
某種程度而言,地圖將田野資料以資料庫的形式呈現給觀眾,具備一定程度的實驗性質。藉由資料攤平展示、使觀眾在有規則下看似自由的,在零散的空間中選取其所想選取的資料。對於南北線常民記憶這個行動而言,是種尚未形成強大話語權、結構,初步與外界對話的嘗試。
地圖是我在田野踏查中,除了在地常民記憶敘事、田野者蒐集地方影像外,關鍵且具影響力、話語的媒材。原因在於意識到在糖鐵的田野執行過程中,幾乎是透過地圖上的訊息(譬如鐵路與相關設施週圍地方、聚落位置、商業地點位置、當地道路配置等),決定田野地點、採集對象,網路地圖的資訊幾乎左右了我們對於田野的探索,也就是說某種程度而言,田野者的話語很大一部份包含地圖資訊的投射。當網路地圖出現及普及後,常民記憶蒐集的田野不再是靠田野者依照其意志的地毯式搜索,取而代之的是由地圖的資訊,使得田野者快速進入現場、確定目標,在田野的意識上有大幅的轉變,或許是田野效率提升、或許更方便、或許是被既有資訊左右、或許也忽略許多記憶,當然在現在網路電子地圖的時代,我們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行動 ,也成為地圖資訊來源的機制之一。因此我想將這樣的感官顯現在作品中,因為這是田野者、在地常民、引路人之外最大的話語權,其話語權影響力甚至超越引路人。
方法上將完成的各地方敘事的片段,上傳至網路空間,並以Google My Map的簡易GIS技術,製作探索地圖,地圖中標示田野地點,並在地圖上標示中嵌入各個完成的片段網址連結。此作法可以試圖呈現透過網路地圖決策田野、間接影響採集記憶內容的感官,並同時可達成攤平看待各地敘事。同時這樣的方法,也是具備延伸性的,常民記憶既然是無限大的,就不應該設下框架浪費其延伸性,在現有的目標地方採集完後,是有機會可以繼續延伸,採集台灣各地更多的糖鐵常民記憶,將是可以持續進行的行動。